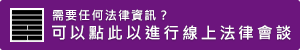「肛交」能否構成通姦罪?
律師回答: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通姦」,係指由於男女雙方合意,而為姦淫;和姦係指與有配偶之人互相合意,而為姦淫行為;姦淫係指男女交媾行為。而以狹義而論,僅限於性器交合,而肛門一般並非性器,但相較於口交,肛交在文義及歷史上與姦淫者相當,關於這個問題的實務見解如下:
關於口交部分不構成通姦罪,此有91年11月06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甲男係有配偶之人,乙女亦明知甲男係有配偶之人,二人仍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一日於台北市內湖區某處進行口交,請問甲男、乙女是否分別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前段、後段之通姦罪及相姦罪?
討論意見:
甲說:刑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稱性交者,謂左列性侵入行為:一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之行為。二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之行為。依刑法前開條文之規定,甲男、乙女所為之口交行為,即合於刑法第十條第五項第一款之所謂性交行為,而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通姦係指和姦,姦淫係指異性不正常之性交,則甲男、乙女所為口交既屬性交,即應分別成立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前段之通姦罪及同條後段之相姦罪。
乙說: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通姦」,係指由於男女雙方合意,而為姦淫;和姦係指與有配偶之人互相合意,而為姦淫行為;姦淫係指男女交媾行為,而修正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前,口交係屬姦淫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色情行為。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立法院修正通過刑法第十條第五項有關性交之定義,亦同時修正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百條...,均將上開條文內有關「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修正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修正後刑法之「性交」範圍較「姦淫」為廣,而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與修正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同屬刑法第十七章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惟該章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之「姦淫」均與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性交同時修正,而同章第二百三十九條之「通姦」或「相姦」則未與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性交」同時修正,顯係就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通姦或相姦,仍維持原來該條係指男女姦淫行為而不擴及修正後之「性交」,是本件甲男、乙女之口交行為尚不構成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前段、後段之罪。
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
審查意見:採乙說。
研討結果: (一) 討論意見甲說第六行末句「即應分別成立犯‥‥」之「犯」字刪除。乙說第一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通姦』‥‥;和姦‥‥」修正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所稱通姦‥‥;所稱相姦‥‥」;第三行「色情行為」修正為「猥褻行為」;第六行末句「而」字修正為「因」;第九行末句「而」字刪除;第十行「與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性交』」等字刪除。 (二) 照審查意見通過。
肛交則構成通姦罪,此觀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102年度上易字第26號所示:
本院透過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目的性解釋及合憲性解釋,認為肛交仍屬刑法第239條所規範之「通姦」及「相姦」行為,茲詳述如下:
1、由文義解釋角度觀察:(1)從刑法第239條之沿革以觀,民國元年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第289條係規定:「和姦有夫之婦者,處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17年中華民國舊刑法第256條則規定:「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最高法院17年10月13日決議意旨因而認為「通姦指和姦言」。而「和姦」乃是相對於刑法修正前之「強姦」而言,指男女雙方合意,而為姦淫行為,僅在行為主體上限於「有配偶之人」,從而刑法第239條所規定之「通姦」、「相姦」行為,其犯罪行為即指有配偶之人與人為姦淫行為、與有配偶之人為姦淫行為之謂。而「姦淫」行為之定義,與刑法修正前第221條強姦罪所稱之「姦淫」解釋上應屬相同。(2)「姦淫」之意義,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係指「男女間不正當的性行為」…依其字義,「男女間不正當的性行為」,並非當然即可排除「肛交」行為。經進一步查詢「性行為」之意義,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係指「男女交合的行為」…「交合」係指「性交、交配」…。而「交配」解釋上雖僅限於男女生殖器之接合,惟就刑法意義上之「姦淫」行為(或性行為),顯非僅只於「交配」行為,亦非從父權或貞操之概念出發,從而刑法上之「姦淫」行為,是否得單純由字義解釋上得出,狹隘的限於男女「生殖器」之接合,解釋上非無討論空間。(3)而何謂「姦淫」行為,又是否包含肛交行為,學者間有不同見解,有認為所謂「姦淫」係泛指違反性倫理規範之性交行為。稱性交行為為「姦淫」乃用以顯示對於此種行為之「非價判斷」(Unwerturteil)(參林山田著,刑法特論(下),再修訂三版,第646、647頁,79年9月),亦即並未將肛交行為除外於「通姦」、「相姦」行為外。有認為「一切之姦淫罪須有姦淫婦女行為。所謂姦淫婦女行為,乃男性將其生殖器插入婦女生殖器官之行為。倘男性之生殖器官並非插入婦女生殖器官,不能認為姦淫婦女行為,例如雞姦行為,非姦淫婦女是。」(參蔡墩銘著,中國刑法精義,7版,第428頁,80年10月)。惟並未說明何以姦淫行為僅限於男性生殖器官插入女性生殖器官之理由。有認為「所謂『姦淫』,指男女間不法性交而言。同性間之淫行,或異性間除性交以外之淫行,均屬猥褻行為,而非姦淫,如雞姦行為是」(參褚劍鴻著,刑法分則釋論(上冊),2版,第611頁,75年2月)。其中雞姦,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係指「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六部成語註解˙刑部:『雞姦:兩男相姦也。』亦稱為『男風』」…,惟對於何謂「異性間之性交」,則未做說明,亦未將之明文排除在外。有認為「稱『姦淫』係指男女交媾行為而言。本條定為對於婦女姦淫者,則所以表示姦淫之意義,限於異性間交合之謂。是而同性間之淫行,或異性間除性交以外之淫行,均屬猥褻行為,而非姦淫。」(參王振興著,刑法分則實用增修本第二冊,第406頁,83年6月)。而「交媾」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係「本指陰陽二氣交合,後泛指性交、交配。」…亦即「姦淫」係指男女性交行為。有認為「基於解釋論之立場,刑法既已將口交及肛交規定為性交,以性器進入他人性器之性交行為為通姦,則以性器進入他人之口腔或肛門之性交行為,亦應認其為通姦。否則,一方強迫他方為口交時,屬於強制性交;雙方同意為口交時,則僅為姦淫,解釋上即有前後無法一貫之嫌。惟倘立於立法論之立場,誠如否定說所言,第二三九條之『通姦』、或『相姦』,既未與刑法第一○條第五項之性交同時修正,得認為係立法者『有意的沈默』,而屬於立法者有意不予規範之『法外空間』。因此,將口交或肛交認其不屬於通姦行為,亦有其道理。」、「惟如前所述,通姦罪屬於『無被害人之犯罪』,實有如以除罪化之必要。因此,如將口交或肛交認其不屬於通姦行為,則因通姦罪在適用上逐漸空洞化之結果,寖假亦可達到除罪化之目的。是以,比較言之,應以否定說所持見解為妥」(參甘添貴,妨害婚姻與口交通姦,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2期,第149頁,2003年1月)。從而除蔡墩銘教授明文認為「姦淫」行為僅指男性生殖器官插入女性生殖器官,甘添貴教授站在立法論及除罪化之立場,認為修法後口交或肛交行為,不屬於通姦行為外,通說之見解認為「姦淫」係指男女間「性交」行為,或更進一步指男女間不正常之性交行為,惟對於何謂「性交」行為,則並未再予解釋,是否當然可認為學界通說認為男女間之「肛交」行為不屬於「姦淫」行為,亦不無疑問。(4)就實務見解而言,亦認為姦淫行為,係指異性間不正當之性交,猥褻係指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他人之性慾,在主觀上欲以滿足自己色情者是(最高法院74年度臺上字第6056號判決意旨參照)。雖最高法院著有判例認為「強姦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分,採接合說,衹須陰莖之一部插入女陰即屬既遂,不以全部插入為必要,而女方之處女膜有無因姦破裂,尤非所問。」(最高法院58年度臺上字第51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兩性生殖器接合構成姦淫既遂一節,係以兩性生殖器官已否接合為準,不以滿足性慾為必要,申言之,即男性陰莖一部已插入女陰,縱未全部插入或未射精,亦應成立姦淫既遂,否則雙方生殖器官僅接觸而未插入,即未達於接合程度,應為未遂犯。」(最高法院62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判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46年度第2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一)決議亦認「強姦罪之既遂、未遂,應依院字第一○四二號解釋以陰莖插入女陰為既遂」,均敘及兩性「生殖器接合」,惟前開見解均在論述強姦罪既未遂之判斷標準,當不能以此即反推實務見解認定姦淫行為僅限於男女生殖器之接合。(5)參諸刑法第221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時之立法理由,理由一係認「原條文中『姦淫』一詞其意為男女私合,或男女不正當之性交行為,不無放蕩淫逸之意涵,對於被害人誠屬難堪,故予修正為『性交』」。理由二復認為「強制性交罪之被害人包括男性,故修改『婦女』為『男女』,以維男女平權之原則。」則立法理由對於姦淫之定義,與前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學者之通說及實務見解係屬相合,而刑法之所以將「姦淫」修正為「性交」,並非在於「姦淫」與「性交」本質及內涵上不同,而係因「姦淫」帶有負面評價(即林山田教授所謂「非價判斷」),為避免被害人難堪,始將文字改為「性交」。則參諸同時修正之刑法第10條第5項就性交係定義為「稱性交者,謂左列性侵入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之行為。」則包含肛交行為(包括同性間及異性間),準此以觀,修正前刑法之「姦淫」行為,自包含以男性性器插入女性肛門之肛交行為(排除同性間之肛交)。
2、由歷史解釋角度觀察:(1)由前開文義解釋分析可知,刑法修正前所謂「姦淫」即指男女間不正常之性交行為,未將肛交排除在不正常性交行為外,則刑法修正後係將帶有負面評價色彩之「姦淫」還原為中性意義之「性交」,並擴及於同性間之性交,且「性交」之內涵,在修法前後,則未改變,從而縱使刑法於88年間,將「姦淫」均修正為「性交」,然刑法第239條文字並未隨同修正,男女間肛交行為仍屬「姦淫」行為,解釋上並無疑問,不存有修法後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是否適用刑法第10條第5項性交定義之命題。惟退步言之,倘將刑法第239條之通、相姦要件採較狹義解釋,認僅指男女交媾即性器官接合之行為(如上揭臺灣高等法院91年法律座談會結論、蔡墩銘、甘添貴教授之見解),而非較廣義如刑法第10條第5項所定義之性交行為,且88年刑法修正時刑法第239條與修正之刑法第240條、第241條同屬刑法第17章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而該章刑法第240條、第241條之「姦淫」均與刑法第10條第5項之「性交」同時修正,第239條之「通姦」或「相姦」則未與刑法第10條第5項之「性交」同時修正,是否為立法者「有意的沈默」?亦即立法者之主觀意思在維持刑法第239條規範之行為態樣不變,僅適用於男女生殖器之接合行為?此即應透過歷史解釋為之。(2)立法院於88年3月30日修法時之所以將「姦淫」變更為「性交」,提案理由乃稱「現行刑法強姦罪、準強姦罪(第221條)、輪強姦罪(第222條)、乘機姦淫罪(第225條第1項)、姦淫幼女罪(第227條第1項)及詐術姦淫罪(第229條)以『婦女』為犯罪之客體,此乃囿於傳統對於『姦淫』與『猥褻』性質之區分,認為『姦淫』只有男性可對女性為之。實則『姦淫』不僅男性可對女性實施,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之間亦可發生,其間端視行為人之犯意及姦淫態樣之歸類而已。例如:行為人以姦淫之意思為口交、肛交或以異物插入被害人之生殖器或肛門,其傷害絕不只單純的於『猥褻』而已,實無不能以『姦淫』看待之理。又查,『姦淫』一詞其意為男女私合,或男女不正當之性交行為,不無放蕩淫逸之意涵,對於被害人而言,誠屬難堪。是否繼續使用『姦淫』一詞,亦不無斟酌之餘地。」故將「現行刑法『妨害風化罪』章、『姦淫』一詞,一律修正為『性交』行為。對於肛交、口交或以異物插入被害人之生殖器或肛門者,以『性交』論。」(參謝啟大等,刑法「保安處分」「妨害風化罪」「妨害自由罪」章(部分)修正說明書,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13期,第201頁、第202頁),可認該次修法之主要目的,依提案立法委員之意見,在使原被認屬猥褻之口交、肛交或異物插入行為,納入修法前之「姦淫」概念中;另一方面,則以詞義上較中性之「性交」取代被認為有非價判斷之「姦淫」,其間對於刑法第239條,則無討論(又提案立法委員雖認為肛交、口交等行為係以「性交」論,然修法後刑法第10條第5項之條文結構,肛交、口交即為性交態樣之一,並非準用,從而立法者似認為性交行為本即包括肛交、口交等行為,則「姦淫」既為不正常之性交行為,解釋上「姦淫」自無不能包括男女間「肛交」之理),未見立法者係有意將刑法第239條排除在刑法第10條第5項適用範圍外。迄至94年2月2日,立法院再度針對刑法第10條第5項之性交定義進行修正,其立法理由則為「為避免基於醫療或其他正當目的所為之進入性器行為,被解為係本法之『性交』行為,爰於序文增列『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文字,以避免適用上之疑義。另為顧及女對男之『性交』及其他難以涵括於『性侵入』之概念,併修正第五項第一款、第二款,增訂『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以資涵括。」可認該次修法之目的,係為解決88年修法增列「性交」定義後所產生實務上適用之困難。修法歷程中,僅司法院代表曾於92年5月5日在立法院召開之公聽會中提及「至於性交的定義問題…法院同仁認為如果要嚴格區分性交關係,則對於過去講的姦淫關係、通姦關係、性的關係、猥褻關係,要不要予以區分?…」(參見法務部編印,2005年中華民國刑法暨刑法施行法修正立法資料彙編上,第401頁);惟其後之各次讀會中,立法委員對於司法院代表所提出之前開問題,仍無任何討論。是就上開立法史料觀之,立法院針對刑法第10條第5項修法增列「性交」定義後,同法第239條雖未隨之進行文字修正,尚不能據此而謂該條文字係有意地保留,或認為係立法者「有意的沈默」。
3、由體系解釋角度觀察:法律規範身為一個價值體系,其最基本要求即為貫徹其外在及內在體系上之無矛盾性,否則將導致平等原則之違反,而不得違反平等原則、禁止原則,對於立法者與司法者同有拘束力。因此探討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如何解釋,則必須透過體系性思考,求與其他條文間體系之一致性。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在刑法法典體系上係列在第17章「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中,而家庭為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基本且重要之組織,家庭則以婚姻為基礎的社會單位,合法健全的婚姻,為健全家庭的根本,該章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及保護家庭的組織與功能,所要保護的法益,即係婚姻制度的安全,及家庭結構的安全,並家庭對其子女的監督權。本罪章規定之罪名計有:重婚罪、同時婚罪(第237條)、詐術締婚罪(第238條)、通姦與相姦罪(第239條)、和誘罪(第240條)、略誘罪(第241條)、移送被誘人出國罪(第242條)、收受藏匿被誘人或使之隱避罪(第243條)。則88年刑法修正時既將同屬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之刑法第240條第3項、第241條第2項、第243條第1項,「姦淫」2字改為「性交」,立於相同罪章之刑法第239條通姦罪及相姦罪,站在法益保護婚姻及家庭健全安全圓滿,與其他修正條文並無二致,倘予以差別待遇,認僅能依據修正前「姦淫」之概念予以解釋,且「姦淫」之概念採取狹義見解,限於男女生殖器之接合,則非無違反實質平等之虞。尤其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刑法第221條、第222條、第225條第1項、第3項、第226條、第226條之1、第227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228條、第229條,及第26章「妨害自由罪章」之刑法第298條第2項、第3項、第300條中與「姦淫」有關之文字,均同時修正為「性交」,何以單獨將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予以區別,為不同之對待?尤其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均略為「原條文中『姦淫』修改為『性交』,參考第二百二十一條說明一」,亦即將刑法涉及「姦淫」二字之條文皆修正為「性交」,則當不能以刑法第239條條文文字上非「姦淫」2字,而係「通姦」、「相姦」,立法者因而漏未將之修正,即認有其特殊性。從而基於體系之一致性,自應與其他修正條文為相同解釋,一體適用刑法第10條第5項關於「性交」之定義,始能維持刑法體系之一體性及文字用語之一致性。
4、由目的性解釋角度觀察:德國法學家耶林(Jhering)在其著作「法律中的目的」(Der zweck im Recht)中指出「目的是所有法律的創造者」。法律解釋即應透過目的性觀點,以確定法律的內容及意旨。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之立法目的,依91年12月27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54號解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所載,係認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參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62號、第552號解釋)。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性行為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惟依憲法第22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受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婚姻關係存續中,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為如何之限制,以及違反此項限制,應否以罪刑相加,各國國情不同,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定之。婚姻共同生活基礎之維持,原應出於夫妻雙方之情感及信賴等關係,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以刑罰手段限制有配偶之人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自由,乃不得已之手段。然刑法所具一般預防功能,於信守夫妻忠誠義務使之成為社會生活之基本規範,進而增強人民對婚姻尊重之法意識,及維護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倫理評價,仍有其一定功效。立法機關就當前對夫妻忠誠義務所為評價於無違社會一般人通念,而人民遵守此項義務規範亦非不可期待之情況下,自得以刑罰手段達到預防通姦、維繫婚姻之立法目的等情。則首應觀察者,釋字第554號解釋所用文字,並非囿於「姦淫」2字,而係以有配偶之人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稱之,並無拘泥在修法前「姦淫」2字之意。其次釋字554號解釋將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之立法目的,定位在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而以刑罰手段限制有配偶之人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顯非基於保護夫權或有配偶之人之貞操,當不能再以貞操之觀念,強調姦淫乃是女性生殖器之被侵入,而應視何種行為將違反夫妻忠誠義務,並危及婚姻之存續來判斷何謂通姦、相姦行為。而肛交行為乃是嚴重悖於倫理評價之不正常性交關係,縱使一般夫妻亦難以輕易嘗試,對於違反夫妻忠誠義務,及對於婚姻關係圓滿之破壞,實不亞於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甚至更甚於後者,從而以刑法第239條通姦、相姦罪規範目的而論,通姦、相姦行為自應包含肛交行為。
5、由合憲性解釋角度觀察:至於倘在文義上採狹義解釋,將通姦、相姦行為限於異性間生殖器之接合,然透過其他解釋,將姦淫行為之概念及於肛交行為,亦即擴張通姦、相姦行為之態樣,是否導致有違憲之虞?就此,以肛交方式為通姦、相姦行為,畢竟為少數之例外,惟就法益之侵害,卻更甚於一般性交行為,衡酌通姦、相姦罪係處最重本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刑法第61條之輕罪,依同法第245條第1項復為告訴乃論罪,刑法第239條第2項並規定,經配偶縱容或宥恕者,不得告訴,對於通姦、相姦罪增加訴訟條件之限制,已將通姦、相姦行為之處罰限於必要範圍(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5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不致使性行為之自由權受到不當之限制,應與憲法之規定尚無牴觸。…綜上所述,被告2人及辯護人上訴主張肛交行為不該當於刑法第239條之要件云云,自無可採,其等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瀏覽次數:4179